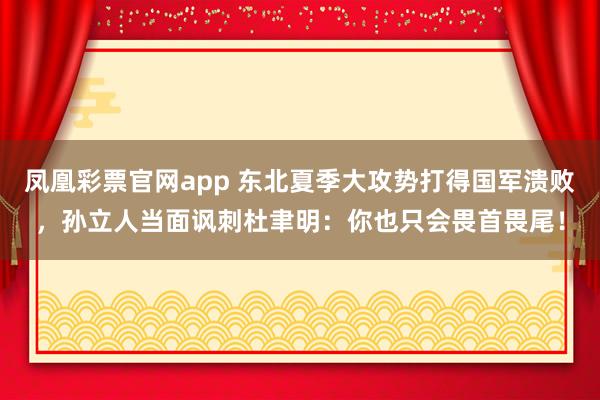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七年五月初,嫩江岸边仍残留着早春浮冰。列车汽笛划破黎明,北安站月台塞满了穿灰布棉衣的战士,肩上擦得锃亮的步枪随着节奏起伏。没有誓师大会,也没有豪言壮语,只有一张张布满风霜的面孔与仓促分发的干粮。进攻的令旗早在前夜递到各纵队,几位主官把薄纸折好塞进怀里,紧跟着便是铺天盖地的调动。

从北安到四平,七百余里铁路纵贯平原,沿线重镇星罗棋布。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把这条线比作“竖琴的弦”,只要在要害处用力一拨,整条“弦”便会哀鸣。东野夏季大攻势,正是从这根“弦”的最北端开始。
有意思的是,就在北满诸部欲南下的同一天,沈阳小南门外的军用机场上,蒋介石的座机也正预热。蒋此行为坐镇东北前线,预计隔天抵达长春。然而,电报机里不断跳出的战况却让指挥链条愈发紊乱——“榆树已失”“江密峰被破”“扶余江面敌船增多”,密集的捷报将南北满即将会师的轮廓推到了幕前。
再把镜头移向沈阳城内。杜聿明掐着鼻梁,一夜未阖眼,作战地图上的红蓝箭头相互缠斗,标记用的红墨水在灯下已近干涸。就算外人不说,他也明白:自己手里的牌很少,可天南海北的援兵请求却如雪片般飘来。更糟糕的,是来自南京的催促。蒋介石急切要求“确保松花江以南要塞、四平—沈阳交通枢纽”,言下之意仍是“守”。
杜聿明非不懂取舍,可每次提及收缩防御,都被质疑是畏战。不赦将军,谤言先至,进退维谷。恰在此时,孙立人奉命离开虎贲之师,转任东北保安副司令。官阶看似晋升,实则被剥离兵权。临行前他接受香港《星岛日报》记者访问,被问及对东北战局的看法,孙立人抿嘴冷笑:“杜长官向来畏首畏尾,良机与他擦肩不稀奇。”只有一句,却震荡军中。
东北的夏风还未真正吹热,东野的十万主力就已分三路泻向南北满结合部。西线是“红色铁拳”一纵与二纵,目标怀德;东线则由洪学智六纵领衔,剑指桦甸、江密峰;南线,韩先楚三纵、曾克林四纵早早盯住沈吉铁路,把梅河口定为“楔子”。这么大的摊子同时开火,绝非只为抢地盘。有老兵回忆道:“那年打的是补给线,补给线一断,他们再多兵也没法子转身。”

八日深夜,扶余江畔的隐蔽船只被蒙布拉开,几百条门桥板顺流而下。工兵们只留一个手势——一根手指指向南岸,随后消失在夜色。等到拂晓,怀德方向已经传来粗大的炮声。怀德的守备主力是孙立人遗留下来的新三十师九十团,加上保安团五千余人。九十团团长项殿元刚立足未稳,突然遭到两纵队包围。“跑?守?”他只来得及在电话里吐出一句:“可否弃守?”话音传到长春指挥部,却被截得只剩“弃”字。
杜聿明咬牙下令:“能守必守,救援部队已出发。”援军是谁?新一军新任军长潘裕昆与七十一军陈明仁,各率两个师沿中长铁路南北并进。可他们一步三停,生怕再陷德惠式口袋。孙立人早有预感,他在离开长春前便记了两页兵要地志交潘裕昆,末尾批注:“怀德撑不了几天,切记勿恋战。”惜乎话未入心。
十四日正午,怀德外围工事被迫火力间接压制,战壕内传来陆续白旗。刘震稳住火舌,故意留下四百伤兵诱敌。陈明仁在大黑林子徘徊,一刻钟内三次电令部队:向北进二十里、停止、再进十里。师部电台里甚至传出他低声自语:“救还是不救?”同参谋答:“将军,请定夺!”两句对白,成为日后研究阻援战心理战的典型范例。
暮色下,怀德最后的枪声停息。西线主力立即转作穿插,对被拖住的七十一军八十八、九十一两个师痛下杀手。不到三小时,八十八师师长韩增栋毙命,九十一师仅剩一团逃向昌图。杜聿明此刻才批准弃农安,但那里的八十九团几乎已被围。所幸林立的玉米秆为国军遮掩,残部钻出封锁线,疲惫入长春。
与此同时,邓华纵队从康平斜刺里插下,冀热辽程子华部在赤峰、宁城、围场一线翻山越岭。冀察热辽解放区当时只有五个野战旅、两个游击旅,外界普遍担心根基太浅,然而石觉的第十三军也好不到哪儿去——八十九师在红石镇折损殆尽,五十四师还在四平苦撑,承德只剩孤零零的第四师。程子华“以空打空”,却靠强行军连拔十二座据点,黄土岭上的信号旗夜夜不息。

攻势越来越宽,真正的重头戏还在长白山脉另一端。南满部队整整憋了半年,弹药补给常靠地窖藏粮背山翻岭。如今北满来电:粮弹可接济,且要会师。临江指挥所里,陈云将这份电报读给身旁参谋。只一句:“北满主力义无反顾支持南满。”屋内气氛顿时不一样,很多干部记得,那一晚临江江面月色很亮。
三纵、四纵主攻梅河口,是打通南北咽喉的必经之战。梅河口守军是第十八师与一八四师,兼旅顺北上之兵。杜聿明命令“固守至死”。他唯一的机动王牌是廖耀湘新二十二师,再拼凑暂二十师、五十四师各一团,组为突击兵团,企图从侧后给南满主力一刀。
十五日,新二十二师刚进南山城子,还在研究地图,四门山炮与一百二十迫击炮就从四面倾泄。“走!”廖耀湘不得不撤。这支曾在沙岭、四平两挫三纵的劲旅,损兵逾千,被迫北退铁岭。久憋怒火终得纾解,韩先楚调转十师,在炮火掩护下扑向梅河口。城头炮零乱,守军无线台呼叫增援却只收到长春空空荡荡的回电。
十九日,梅河口告破,一八四师番号随即从编制表上抹去。曾克林率分兵同时敲开东丰、西安,掐断了沈吉铁路腰眼。更令杜聿明焦头烂额的,是通化、新宾、本溪接连失落,铁岭以南电报线一夜无声。北满、南满终在昌图一带握手,七个月来的“带子形孤局”被彻底撕碎。
沈阳东塔机场上空,蒋介石的座机终于落地。观礼的原计划取消,迎面而来的,是一个被连环红线切割的东北地图。蒋提出收缩防御,杜聿明不得不低头,着手撤并。但就在机关忙于编组防区时,前线传来“昌图、开原俱陷”,东野八个师已逼四平。

四平,当年国军在此留下无数弹孔与勋表。将士心底残存着“去年能守住,今年也能”。然而今昔已异。东野兵力增长三成,火炮翻倍,战术成竹在胸。杜聿明仍想重复旧式机动:以外线装甲、炮兵打草原迂回,可汽油短缺、铁路线屡断,坦克拖车常常半路抛锚。空中支援更因美援油料额度紧缩而捉襟见肘。
彼时的战况,凤凰彩票welcome坊间只见到数字,却看不到决策背后的拉扯。杜聿明清楚地感到,每一条退防电文都像是一纸自我否定。可若仍按南京口径寸土必争,结局只会更惨。他对身边副官叹道:“守不住也得守,这就是命。”副官低声回:“将军,撤也不是坏事。”短短十一字,再无回响。
五月尾声,热河方向再传捷报:冀东部队牙切宁大开羊腔,一路斩断锦承公路与锦古铁路。至此,东北国军呈“T”字形断裂,沈阳与长春腹背一时难顾。盛京满城传言:“东野兵锋最快三日可抵辽河。”夜半街头,不时有难民推着木车北逃,远处可见燃烧的仓库映红天际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如果说春季攻势已让国军尝到疼痛,夏季攻势则是撕碎神经的手术刀。短短二十余天,新三十师九十团、七十一军八十八师、一八四师相继覆灭,新二十二师受挫,合计损失三万五千人以上。南北满会师,解放区面积增加五万平方公里,控制人口骤增三百万。

此时再回看人事更迭:孙立人离开新一军,杜聿明独撑前线,蒋介石亲赴沈阳,王耀武声援乏术。环环相扣,最终酿成了国军在东北的战略崩盘。史家往往讨论孙、杜二人龃龉,实则折射的是当时国府高层对于“守”与“放”的判断失衡。放一步或许尚可回身,死守则连退路都不剩。
值得一提的是,东野此轮攻势并非单纯依赖数量,而是指挥链简洁、目标集中、后勤跟进。陈赓后来总结说,最关键的是“线段穿插”,避实就虚,割断交通,让对手每走一步都像踩在玻璃渣上。事实证明,这种战法在东北平原极为有效,国军的堡垒式体系被迫变回流动作战,却失却了机动先机。
六月初,四平攻坚战打响,双方皆知这座城将决定东北下半年走向。杜聿明再次把最硬的牌——李弥、郑洞国、廖耀湘集中于四平外围,甚至动用了最后的十七辆M5A1轻坦。与此同时,林彪却发电给所属各纵队:“宁失地,不失时;宁少吃,不停打。”一句十三字,定下攻城底色。
炮声滚滚,飞扬尘土中夹杂初夏的槐花香。四平街巷再度成为火海。与去年不同的是,国军增援线路被切得支离破碎,弹药、口粮、药品难以跟进。第三昼夜,刘亚楼在前线观察所说:“敌未崩,已虚。”第五昼夜凌晨,火车站、保安队大楼相继失守。七日清晨,国军开始突围,溃兵沿铁路线南逃,坦克来不及加油被炸毁于路基。四平,终于被写进东野的战果簿。
当日午后,杜聿明在沈阳总司令部签发电令:“全线收缩,退保沈阳—营口—锦州。”电令发出时,电话那头的参谋已听见他重重叹息。又过数日,蒋介石返回南京,在飞行日志上只写了四个字:“东北凶危”。东北夏季大攻势,以东野大捷、国军溃败告一段落,却也为随后的秋季攻势埋下更凶猛的引线。

后续:夏季攻势的战略回声(约八百字)
夏季攻势结束后,东野各纵队并未立刻停顿,而是利用短暂整补迅速固化战果。北满第一、第二、三纵队临时组成“前卫集群”,在铁岭以南布设纵深警戒;南满部队则分兵巩固辽东、旅大外围。此时的战场,表面进入相持,实则暗流涌动。

首先是后勤。北满虽地广物丰,但铁路桥梁多被国军炸断,物资南运仍需人背马驮。一纵后勤处统计,仅六月上旬就调拨步枪子弹三百五十万发、迫击炮弹四万余发,全部依赖肩挑背负与草鞋驿运。运输负担催生了“民夫轮班制”:每乡每夜必须派足定额民工,确保补给带到前沿。
其次是空中威胁。驻沈阳的美制B-25、P-51频频出动,对阜新至法库一线实施轰炸扫射,意在扰乱东野后方集结。针对这一情况,洪学智干脆将纵队辎重分作三股,以夜行昼伏的方式逼近沈阳外围,同时要求部队“宁走羊肠,不走官道”,有效减轻了损失。
再者,国军内部的裂痕愈加明显。孙立人虽未再掌实权,却在文电与报刊上持续放话,批评杜聿明“迂腐守旧”。这一批评迅速传入前线,道义冲击远大于军事打击。许多国军军官在私下议论:“既然连孙将军都不看好坚守,我们还能撑多久?”士气随之下滑。
同一时间,冀热辽方向的程子华趁石觉回援四平之际,大胆北出御道口,一举夺下古北口以西的密云县城,使得平古铁路多点断流。该战果虽在全国版图上分量有限,却让北平行营如坐针毡。华北“剿总”被迫电示东北:“务必遏制冀热辽之敌南窜。”杜聿明苦笑:自顾尚且不暇。
基于连环崩口,蒋介石与内阁于六月二十六日召开临时军事会议,提出“先保华北,再图东北”的折中方案。换言之,东北可适度放弃,以保存机动力量。然而命令下达层层传递,真正执行时早已晚半拍。七月初,东野侦察部捕捉到国军在辽西走廊修筑第二道防线,规模远逊春季构筑的“松花江—四平—沈阳”一线。

试想一下,如果夏季大攻势没有撕开交通网络,国军或许仍能依托铁路纵深、依靠海空补给打一场持久战。但一旦交通线被彻底切成块状,战场主动权瞬间转手。从五月到七月,东野阵发式攻势与国军被动收缩形成鲜明对比,东北战局的天平因此永久倾斜。
在此背景下,沈阳、锦州成为国军最后的“铁桶”。连年鏖战已让东北城市工业凋敝,然而在两城之间,东野却抢下了几乎所有乡村与交通要冲。到一九四八年初,国军虽仍据守大城市,却如同悬在半空的孤岛,彼此只有空运与浅水港相连。夏季攻势留下的断裂带,成了辽沈决战的天然战场。
总结夏季攻势对后续战局的直接影响,可归纳三点:第一,割裂国军防线,迫使其战略收缩;第二,提升了东野统筹南北满作战的能力,为统一指挥、快速机动做了演练;第三,心理层面重创国军,尤其是对杜聿明与东北行辕的决策威信造成无法修补的裂口。
正因如此,八个月后的秋风乍起,辽沈战役的棋局才一触即发。国军虽有飞机、坦克及海上补给,却再难寻到可整建制机动的通衢;东野则握有完整腹地与充足兵源。两相对照,胜负已在夏季攻势中埋下暗钉,无需任何溢美之词。

 备案号:
备案号: